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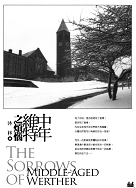
中年維特之煩惱和少年維特有何不同? 作者以細膩的筆觸,娓娓道來。
此故事像是發生在海島一嶼的《未央歌》,但是更成熟、更深入、也更貼近你我維特之煩惱。
故事的主軸描寫一位中年科技人物匡復的心靈成長經驗,他從鄉下到大城市的台北唸書,再到美國。因為年輕,所以流浪;流浪的過程中一直不停地在追尋,從追求聯考的目標,到情感慰藉,之後進一步尋求生命的意義和心靈的寄託。在學業、家境、生活價值、以及對自身與未來的種種茫然中,使他錯過了一次刻骨銘心的戀愛初體驗;即使年歲的增長與閱歷的增加,卻還是無法忘懷那一段失落的愛情,以及發現自己經常陷落於追回失落情感的莫名行動。當他即將參悟,就要找到出路時,卻乍聞意外的訊息,年輕的她……。之後他到底是更為陷落,或是超越了此一失落,獲得重生和解脫?
中年維特與少年維特的煩惱,都因情愛而起,都跳脫不了一個癡字。但作者在故事中所闡述的不只有這層情愛上的深刻感受,還縱深地寫出了那一個年代的台灣社會政經背景、學生們共同記憶的求學生涯和留美生活,還有深沉的心靈與宗教思辯。看似如早年的愛情電影,但卻蘊藏有不著痕跡的生命哲思,甚至有些淡淡的哀傷。他細細描繪,娓娓說來,似乎在寫作者自己,卻更像是那個時代中許多人的綜合體。彷彿有濃厚的自身影子,卻不孤高,踏實平易的述說反而更易於共鳴,更能觸動住在海島的我們,以及也在徬徨中尋覓之人們;會不會這也是你我都曾經歷或夢想過的《未央歌》與「中、少年維特之煩惱」?
……
二姐為爸爸準備了花生米和小魚乾,那是爸爸喜歡吃的小菜,似乎二姐還蠻高興爸爸過來。爸爸坐在茶几前,夾著花生米和小魚乾,當點心吃。匡復到了以後,也坐在一起,夾著這些花生米和小魚乾,吃將起來,這是匡復和爸爸之間特有的共同語言,吃著小菜,東一句西一句,沒頭沒尾地聊。爸爸沒有唸過書,沒有向孩子們談過什麼大道理,匡復也從小沒有留意過爸爸告訴了他那些道理,爸爸也從不在意匡復是否記得他說過那些話,只是也不能期待,爸爸會把孩子的話當真。與媽媽相比,覺得和爸爸在一起是比較自在的,因為不必特別留意那些話不該講,這是多年來的印象。
所以匡復也就和爸爸隨意地聊,聊著聊著,說道:「我想要出國唸書。」
很意外地,爸爸突然暴跳如雷,勃然大怒,幾乎是咆哮地說: 「你要出國? 我那些田賣了也不夠,你別妄想,就算夠,也不可能,我不能把田賣了給你出國,我還要留給你哥哥們。」
爸爸突然生氣,不僅出乎匡復意料之外,也在二姐意料之外,一時之間,二姐不知該如何是好,她一會兒看看匡復,一會兒看看爸爸,不曉得要幫誰講話,也不知該如何圓場,匡復看出她其實不知所措,但強裝鎮靜,…。
匡復這段期間運用理性面對事情的做法,似乎也在這個時候發揮了作用,他想,其實並沒有要爸爸賣田,於是他鎮定地說:「我不需要你賣田,出國的費用,我自己會想辦法。」
講完後,匡復想,此時爸爸正在氣頭上,空口白話,爸爸不見得立刻消氣,剛好那天領了家教的錢,三千五,於是從錢包中拿出來,告訴爸爸:「這是今天家教領的錢,給你兩千,我留著一千五,自己要用。」
爸爸拿了兩千元,氣果然立刻消了。二姐報給匡復感激的眼神,匡復明瞭,此時的她要拿出兩千元也是難的。
理性上,匡復能理解爸爸為什麼會有那樣的反應,他已六十六歲,那幾分田是他一輩子努力的結果,失去了那些田地,對爸爸而言,好像也就失去了這一生。但感覺裡,對爸爸收下他給的二千元,卻覺得有些失落,不是少了錢,而是感到親情不如預期。這段期間,匡復面對人生各種難解的問題,渴望有個強有力的膀臂,幫他解決困難,但爸爸不能扮演這個角色,反而匡復成為爸爸的安慰者。其實,匡復應該習慣的,因為從小到大,匡復對爸爸的瞭解遠比爸爸對匡復的瞭解還多。哥哥姐姐們都認為爸爸很凶,但匡復卻認為爸爸較慈祥,大概因為匡復抓得到爸爸的脾氣,知道如何應付他。但是,此時此刻,匡復尚在感情的創傷和其他困惑當中,還要面對親情衝突的張力,覺得力有未逮。
整個晚上,匡復不禁回想起和爸爸過去的互動,其實大多是快樂的,記得國中二年級時的暑假,早上去學校上輔導課,中午回家後,吃過午飯,爸爸和二哥要去田裡工作,匡復說要複習功課,他們也就由著他,沒有強迫他下田。到下午兩點左右,匡復複習完功課,那天的功課比預期中的容易,所以較早讀完,之後就跑去放風箏。
玩膩了,回家喝水,剛好二哥回來,二哥說:「你不是要複習功課,怎麼沒在唸書?」
匡復告訴二哥,「我去放風箏。」
二哥笑笑地說:「…,不要告訴爸爸,小心他會打你。」匡復和二哥年紀差了十五歲,二哥像是哄小孩般地對匡復說。
「應該沒關係吧。」匡復說,「我覺得告訴爸爸也無所謂。」
「好,那我就告訴爸爸,你跑去放風箏。」二哥開玩笑地恐嚇匡復。
剛好爸爸回來,問說:「什麼風箏?」
匡復說,「我做了一個五角形的風箏,我剛剛去放了,還飛得很高。」
爸爸說:「五角形的風箏能飛? 我跟你去,你再放給我看。」
二哥聽了,目瞪口呆。
爸爸真的和匡復去放風箏,匡復向爸爸說明五角形的風箏如何做,以及其骨架與四邊形風箏的相似與差異之處,還有為何五角形的風箏也可以飛上去。之後,他們就一起放風箏,看著五角形的風箏升上天空,那時覺得和爸爸一起放風箏的感覺很溫馨。
匡復回想這些往事,再對照今天晚上發生的衝突,覺得不勝唏噓! 這一天晚上也就沒有睡好。
隔天,一大早就起床了,因為爸爸平常住在鄉下,習慣早起。匡復也跟著早起,想回去宿舍再補個眠。拖著疲勞的身體,回到宿舍,正想往床上躺,卻看到力立躺在他床上,而且滿身酒味,匡復不禁氣從中來,打算把力立拉起來,或許還要揍他幾拳。於是匡復轉頭先把包包放到書桌,再來準備要找力立算帳,但這時看到書桌上擺著一瓶酒,上面有本日記。日記攤開著,上面是力立的筆跡,匡復無意間看到日記上簡短的一行字:
「上帝,上帝,祢為什麼離棄我!」
不知為什麼,匡復突然對力立有著很深的憐憫。他知道力立的處境更為艱辛,匡復到大學才發現爸爸不能幫他解決困難,而力立在高中時,爸爸媽媽就棄他而去,得自己面對生活。匡復昨晚的感受,與力立相比,實在算不得什麼。於是匡復放下包包,自己去逛校園。匡復繞了一大圈,希望繞得夠久,回來時,力立已經醒來。此刻匡復心裡已經夠煩了,只想讓這件事像是沒有發生過一樣。
匡復自己逛著校園,在這清晨時分,醉月湖、椰林大道相當安靜。他踽踽獨行,想著這一切,愛情,親情,一切都不可捉摸,讀了那些書,還是沒有找到答案,為什麼學校的課程沒有把這些列為必修? 讀一堆中國通史,中國現代史,對解決切身的問題卻一點幫助也沒有,到底還有那些書會提供答案? 再多想一些,或許自己算幸運了,大一時誤打誤撞參加了台大青年社,讀了一些哲學方面的書,因此學會了理性控制自己的情緒,否則昨天晚上恐怕就和爸爸吵了一架,今天早上或許也和力立打起架來。想到這裡,匡復覺得還有許多哲學概念沒有讀清楚,新潮文庫有不少相關的書,應該去買些來看。而想到台大青年社,有一段時間沒有去了,或許該再去看看,到底它是幫忙度過這段痛苦時期的關鍵。
隔天,匡復去台大青年社,看到桐齡在社辦,她現在是社長。匡復在社辦門口,看到她坐在椅子上,光線從門口對面窗戶的霧化玻璃照射進來,柔和地映照出她的側面,她雙眼看著正前方,凝神,若有所思。匡復卻似乎看到她表情慈祥,但略顯歲月的風霜,彷彿過去某個時候看到的一幅慈母畫像。畫像中,眼光慈祥,但臉上卻難掩擔憂,一種經歷歲月,因艱難刻劃而成的面容。匡復感到奇怪,為何桐齡的側影讓他覺得像是看到慈母畫像?
此時,桐齡忽然轉身,看到匡復在門口,他們目光相對,桐齡的慈母面容瞬間轉換回年輕少女的臉龐,如大一時看到的模樣,但眼光中流露出對慈父的渴望。在他們目光相對後的一剎那,匡復幾乎要奪門而逃,他承受不起桐齡眼光投來的渴望,他自己都已心煩意亂,無力再幫桐齡承擔。桐齡也瞬間看出匡復眼神的閃躲,帶點失望地收起她的渴望,然後若無其事地轉頭和學妹討論事情。
然後匡復進去社辦,瞭解到此時台大青年社已在風雨飄搖當中,因為學校對台大青年社的補助經費大幅減少,使得要繼續出版台大青年雜誌有很大的困難,財務上的難題使得大家士氣低落。有人想乾脆結束台大青年社這個社團,有人覺得台大青年這個雜誌提供了許多大學生珍貴的論點,報導大學生對國家社會的理想和憧憬,應該設法留存;有人就單純地不捨在這裡建立的情感。桐齡在多位社友的懇求下接下社長,但面臨財務困境,士氣低落,以及在此困境中的流言蜚語,有些心力交瘁,但又不捨棄之而去。
在困境中,或許當家的女性自然流露出母愛般的光輝,使得匡復看到她時,潛藏的戀母情節不自覺地浮現。而桐齡到底也只是和匡復一樣的年紀,匡復內心因困難而煩亂,桐齡又何嘗不是,所以在看到匡復的那一瞬間,對尋求如父愛般之有力依靠的渴望就不自覺地流露。為什麼?男性在困難時渴望母愛,而女性在困難時渴望父愛?是否人的內在本就潛藏著戀母情節或戀父情節?匡復不禁想起和曉軒碰面的最後一夜,曉軒對他的期待是否也是一樣?曉軒尋求的是男女朋友間的愛情,或是在困境中可以依靠的父愛?而匡復自己呢?他需要的是男女朋友間的愛情,或者也只是在困境中可以依靠的母愛?而到底男女之間的愛情應該是什麼樣子?是否其實也只是對母愛和父愛渴望的延續?所謂的靈犀相通,是否只是童稚時期,懵懂無知當中,對父母呵護的簡單期待?而當這樣的期待轉向其他人時,就得不到盼望中的回應?
或許,在社辦門口,當桐齡以渴望父愛的眼神看匡復時,匡復若不是逃避,而是給她正面的回應,他們會…。或是,在和曉軒碰面的最後一夜,匡復若給曉軒正面的回應,結果也會大不相同。他為什麼不敢正面回應? 是否因為是老么,從小起就不必為別人承擔的習慣,叫匡復不敢幫別人承擔什麼?而這也是受到原生家庭所捆綁的型式之一?而另一方面,愛情是否就一定得為對方承擔?即使痛苦也得走下去?就像二姐一邊工作,又一邊自己默默帶著小孩?但看到二姐那樣的情況,匡復真的不敢進入這樣的愛情。
匡復似乎只盼望童話故事中,王子與公主幸福快樂的樣子,但在現實生活中,卻不可得。不然就得看破紅塵,不被情愛牽絆。但不幸地,他也似乎無法切斷對曉軒的思念。人生似乎要做個抉擇,不是得看破紅塵,就是要下定決心,為對方承擔。而如果要為對方承擔,匡復能嗎?他面對生活,面對原生家庭的捆綁,自己都已自顧不暇,心煩意亂,如何有餘力為另一方承擔?
匡復內心思潮洶湧起伏,許多想法盤旋在心中,人生難道就是如此?想要逃離承擔,就會陷入孤單,一種和其他人心靈隔離的孤單;而若要逃離孤單,就會陷入必須為他人承擔的苦痛,即使力不從心,也得咬緊牙關。佛教的出家,到底是看破紅塵,或是逃離負擔?小說中提到清朝順治皇帝把皇位放給尚未成年的康熙,落髮為僧,到底是看開權力的高尚情操,或是逃避家庭責任?而看破紅塵,就是接受並習慣於和其他人心靈隔離的情況嗎?人真能如此嗎?佇立山腳的岩石,不就已經看破紅塵?那何必有生命有感覺呢?像石頭不就好了?可是有感覺就有痛苦。能否存有愛而沒有痛苦?不必為金錢操煩,不必擔憂柴米油鹽,沒有流長蜚短,像童話故事中,王子與公主幸福快樂的愛情真的存在嗎?而他對童話故事中王子與公主的憧憬又從何而來?是因為看了迪士尼卡通或愛情神話而來,使得他不知不覺地要模仿迪士尼故事或神話,想把卡通或神話情節落實在生活中,以致於陷入這真假難辨的情況?或是人的內在本就存在對理想世界的期待?而真實和想像之間是否根本就沒有一道清楚的界線?
他內在的感受是如此複雜,但在社辦裡和桐齡以及其他同學談話時,匡復還是表現出理性的樣子,假裝是沒有煩惱的模樣。或許桐齡看到他逃避的眼光,只會認為他不想淌這趟渾水,根本就不知道他是無力多幫她承擔。不管他是有心無力,或是根本無心,對她而言,結果都一樣,就是她沒有得到想要的幫助。
他回想大一進入台大青年社時,大家都天真無邪的模樣,當時在活動中玩遊戲,互相大眼瞪小眼,好不開心,那時對人生的未來充滿憧憬,想像中的世界幾乎都是美好的。沒想到,到了大三,卻發現原來人生有接連不斷的挑戰,而且未來依然有許多的挑戰,桐齡面對的困難,力立遭遇的苦楚,匡復心中的煩亂,大家都是天涯淪落人,雖然相逢又相識,可是相識又能奈何? 匡復希望能滿懷信心地告訴自己,「我一定可以衝破困境」,然而這似乎只是沒有確據的吶喊!
(摘錄自 “中年維特之煩惱”, 2010 年遠流出版。 )
林清富,電機系1983年畢業,現任臺大電機系教授及光電所所長。 |

